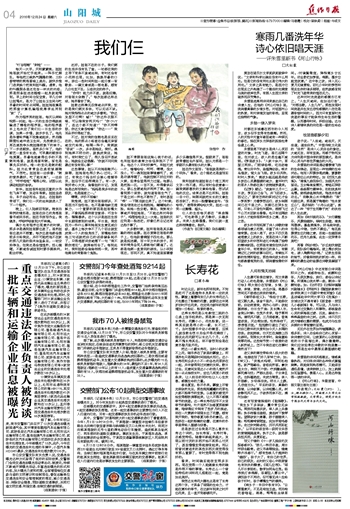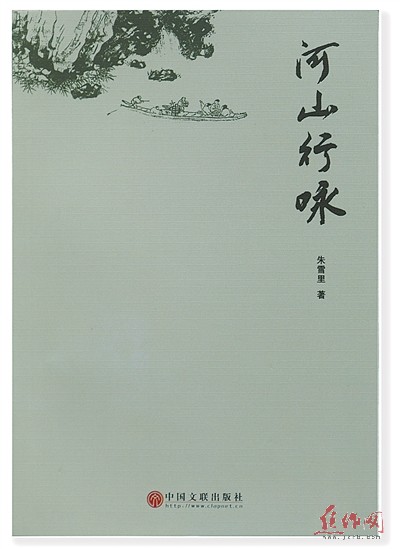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致辞中说:“文学和科学比确实没有什么用处。但是它的没有用处正是它伟大的用处。”文学之具有魅力,是因为它在现实之外构建了一个雅洁的充满爱与美的彼岸世界,有涯人生因文学的滋养而芬芳隽永。
朱雪里选择用诗词来表达自己的诗意人生,在他的《河山行咏》里,流淌着真挚的乡情乡愁,对祖国河山的热爱,和对亲情友谊的珍视,呈现出独特的气象。
乡愁一缕入梦来
对朝在东城暮在西市的今人而言,故乡似乎变得有些模糊。然而,人的天性中对童年寄居地有一种深沉的眷恋,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也常会袭上心来。
朱雪里笔下的故乡是诗人心灵回望的对象,时光飞逝,虽已远隔千里,但对故土、故人的思念毫不减弱。《梦里故乡》:“人家十余户,草屋三两排。门前绿杨柳,宅后老榆槐。青壮田中作,翁媪携幼孩。啄木鸟值夜,萤火虫飞徊。故乡旧风物,时时入梦来。”离故乡越远越是将故乡放在心灵最温暖的地方,童年时代的草木人物都在某个夜晚随梦袭来。
《记梦》题记:“庚寅年三月十二日夜,梦见自己会飞,并飞回故乡,因记之。”要有怎样的深刻记忆才会一梦再梦?为着梦想远行,故乡转眼间已在千里之外,双脚已在异乡生根,只有心不受任何羁绊,频频飞过千山万水回家去看看。也只有远隔故乡的人才能体悟那种思乡之痛,思乡之苦。
故乡的书写拓展了诗人诗歌的情感领域与意义范围,丰富了诗人的诗情背景。在诗人笔下,故乡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,更是在诗人不断回望故乡的怀想和追忆中构建了独特的精神家园。在那里有清贫但快乐的童年少年,有疼爱自己的亲人,有缀满记忆之树的故事与回忆,有牵扯不断的怅惘和留念,那些伸向故乡的诗句都裹着滚烫的泪,倾淌着蚀骨的怀念。
人间有情天地阔
人生最可珍贵在情字,而文学最打动人心的也是情。朱雪里的《河山行咏》很大部分在写情,乡情,友情,亲情,爱情,亦庄亦谐,笔墨芬芳间无不渗透出浓浓的情来。
《清明祭祖父》:“倏忽廿五载,祖父眠九泉。谋食千里外,不能祭坟前。自幼疼爱我,视作心与肝;夜起屡掖被,白日负于肩;及长携入市,食我以时鲜;负笈外求学,暗予零用钱。清明风不暖,三月倒春寒。登高望故里,天边柳如烟。怆然涕泗下,滂滂湿衣斑。”短短数行道出了祖父对自己数年的关爱和如今天人永隔的悲哀。夜起掖被,白天扛在肩膀上四处游玩。到我长大求学时,偷偷塞给我零花钱。这些细节使一个慈爱的老人跃然纸上,怎不令我在追忆往事时潸然泪下?
老父亲的离世带给诗人极大的伤痛,他接连写了好几首悼亡诗,如:《悼父》:“茨淮水呜咽,平阿松柏愁。家严驾鹤去,音容宛然留。豪饮追太白,睥睨万户侯;疗疾踵扁鹊,解民痛与忧;严慈比岳母,子女孝且优。岂料罹绝症,未成古稀叟。亲人肝肠断,乡邻涕泪流。明日入土葬,儿悲斑白头。”平实的语言,真挚的感情,以诗叙事,以诗袒露心灵。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在,痛何如哉?
还有写爱情婚姻的《瓷婚歌》:“我生乡下多弟妹,囊中常空无余钱。洞房花烛喜庆夜,单人床上共妻眠;执手相看泪盈眶,黄连树下拨琴弦。望眼欲穿六寒暑,娇子姗姗来人寰;呱呱嫩啼萦陋室,宛如早莺鸣春田。走过坎坷路途坦,历尽风雨彩虹妍。”以平实的语言将一段同甘共苦的爱情娓娓道来。执子之手,就是要共担风雨,共赏彩虹。
写父子情的《十一岁儿独自约友探春感怀》:“娇儿一秩羽丰盈,周日呼朋去踏青。老父书斋聊独坐,雏禽野外戏春汀。”颇有些被儿子抛弃的“幽怨”。孩子大了,有自己的世界,自己的朋友,此时的父母心中既甜蜜也有淡淡的醋意。《顽儿应考》:“顽儿尽日享轻松,散学如同鸟出笼。临考挑灯亲佛脚,答题坠入雾云中。”调侃孩子不用功,似可看见诗人念给孩子听时,孩子噘嘴生气的模样。
《南乡子·辛卯中秋有怀》:“云雾漫寒天,不见苍穹挂玉盘。雨后桂花香暗溢,绵绵,唧唧秋虫绿草间。/对镜鬓微斑,弹指离乡廿五年。功业渺茫如梦里,难眠,漫步空庭觉夜寒。”在中秋之夜,诗人无心赏月无绪赏桂,回忆少年时的梦想和现实生存的诸多局限,忽然就感受到了时光飞逝带来的惶恐无力。
这种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古已有之,“人生天地间,忽如远行客”,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。那些发现时间流逝并生发出悲怆感慨的人往往是最珍惜时间的人,因为只有直面时光流逝的事实才能保持生命生活的警醒,从而善待时间,积极创造。这与诗人寄情林泉的向往是一致的生命态度。
牧笛渔歌醉夕阳
老子说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中国传统文化里的“自然”是诗人心灵自由的象征,大地无言,却有至美。而感于物而发为诗则是中国诗学的原型模式,是诗化心灵与外部世界撞击的火花。
朱雪里的诗词里涌动着激情飞扬的生命律动,呈现出一种饱满的生命状态。他写人即景涉笔成趣,寥寥数语勾勒出山水的特征。如《泛筏九曲溪》:“清溪九曲筏徐行,如画风光扑面迎。玉女峰高耸霄汉,青蛙石异卧丛蘅。森森翠竹藏禅寺,汩汩流泉和鸟嘤。俯视游鱼翔浅底,悔违本性逐功名。”将静美山水中陶醉的“我”勾画出来,那是属于陶潜的“性本爱丘山”,是苏轼的“小舟从此逝”。表达了一种“恬于生而静于死”的淡泊的人生态度。
再如《林州桃花谷》:“太行藏壑谷,风景独幽妍。绿树生岩壁,清泉泻碧渊。嘉鱼溯溪泳,好鸟绕林旋。但得山中隐,怡然不羡仙。”每见胜景便生出归隐之意,若能一生幽居桃花谷,泛舟九曲溪,此生一定异常丰美吧?
再看《响沙湾》:“沙丘起伏接蓝天,驼队徐行瀚海间。坡上滑沙疾如电,游人陶醉响沙湾。”记录生活里的细节,好像照相机的抓拍一样,将瞬间的最生动的场景在诗歌里凝固下来。
《河山行咏》中还有部分诗词是即兴之作,或感物咏志,或酬和应答,凡朋友聚会,旅行,都会以诗纪事。所谓高山流水琴一曲,赋诗一首酬知音。如:《访乔羽》《访梨林镇赠刘副镇长》《师徒吟》《赠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三十四期中青班同窗》《送孟战福赴华中师大学习》《浣溪沙·京城访友不遇有寄》《画堂春·贺侄儿小春新婚》等,可以说,凡与诗人生命有过交集的人和事物,都被漩进心灵的深海里过滤、沉淀,凝结为一株株晶莹的诗之树。这样,诗不仅仅成为情感吐露的需要,也成为与生活共振的日常智慧的呈现。
无论外在世界如何喧腾躁动,诱惑多彩,诗人总会给自己的心灵留一块诗意的空间,让疲累的心从按部就班的日子里溜出来,偶尔撒撒野。我们应该经常在诗歌的怀抱里靠一靠,那是生命中最厚实最温暖的慰藉。
朱雪里的诗词风格雅正,情感真挚热烈,对旧体诗词的各种体式掌握娴熟,既能做到构思精巧,又能语言通俗易懂,读来朗朗上口,加上韵脚如瓦釜雷鸣,激荡人心。正是这样值得一读的诗词。
(《河山行咏》,朱雪里著,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)
作者简介:文红霞(1972- ),女,湖北秭归人,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,文学博士,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。